被异化的科技与无尽的审查
大约是六年前,我写下了一篇名为《手机承载记忆》的文章,回忆了我从诺基亚到一加7Pro的历程,那是我对科技进步的致敬和对5G时代的憧憬。
其实,回顾上一篇文章,即使是在我高中至大学的阶段,我的倾向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外版手机与国际版固件,从各方面来讲,那台Google Nexus 4对我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至少是它帮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经过了全网怀念的2018年之后,我带着在2018年对未来的憧憬,写下了那篇文章。
然而站在2025年,回望当年,我看到的不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是科技在合规的阴影下被异化和限制,以及这种限制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一步一步蚕食着用户的选择空间。
对功能的阉割和对体验的阻碍,并不是技术发展中的插曲。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持续性的制度模式,这或许影响了我对未来的一些看法和选择。
不将就个屁。
虽然我不喜欢华为的产品和营销风格,但我依稀记得我在一加8Pro的那篇评测文章里表达了我对诸如三星等国际大厂供货制裁的担忧。
不过最终这个制裁是来自于一个不可抗力的层面。
我在初中的时候有阅读科技杂志的习惯,我清楚的记得某一期《电脑爱好者》杂志刊登了一期华为发布Windows Phone手机的消息,余承东在当时对记者说“如果他们(谷歌)不给我们用了怎么办”,这至少印证了在2013年华为已经有了面对国际供应限制的前瞻和预判,乃至后续自主研发Harmony OS的铺垫。
说远了,小米没有坚持自己“为发烧而生”的承诺,8Pro之后大氢也亡了,整个OxygenOS也变成了Fork for ColorOS,一加最终没有带着自己的那根刺,继续兑现自己“不将就”的承诺。
一加回归到了OPPO的子品牌,从小米到锤子再到一加,果然理想主义者的最终结局都是屈服于现实或覆灭。
无功无过,主要还是谷歌和高通的双重不争气,让我选择逃离Android阵营。
双持党的数字游民之路
理想主义的幻灭和火龙先祖复刻之后,我换了iPhone 12 Pro。
苹果对硬件相对保守,回退到60Hz刷新率让我暂时眼部不适,也彻底理解了那句“但用难回”。
在相同的价格下,我在国行12紫色和日版12Pro之间抉择了很久,基于对硬件配置和价格的考量,我选择了后者。
2019年初我在朋友的介绍下第一次接触到了国外运营商的SIM卡,相比Google Voice的虚拟号码也更加干净,不会在注册各种服务的时候被风控,而且在国内漫游也可以连接到一个不那么受限的网络,毕竟一年一百多块钱的价格换来一个非常时期的必要应急手段也是值得的,2020年的日版iPhone也已经支持了eSIM。
后续也是出于价格优势的原因,我依旧选择了日版的14 Pro Max、15 Pro Max和16 Pro Max,在eSIM的便利下,我也体验过了多个国家的网络运营商,这几年我在数字游民这条路上畅通无阻。
“苹果税”是客观存在的,我也确实发现了在iOS上内购充值游戏和点外卖有时比Android平台更贵,所以我也还是保留了Android手机作为备用,除了一加9R,还在日本旅行的时候购买了Nothing Phone 3a,这便是我最近6年对Android的印象,除了功能和硬件上的更新,一切都还是原生的。
审查下的AI缺席与特色eSIM落地
从iOS18发布之时,苹果就官宣了Apple Intelligence接入ChatGPT,但无论是审查层面还是OpenAI自身政策,GPT本身在内地就是不可用的,虽然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时至今日到iOS26.0.1,Apple Intelligence在内地依然没有准确的落地消息。
比较有趣的是我参与过一场针对AI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测试,并且成功诱导AI说出了不当言论。AI要合规的原因在于,人犯了错有人负责,AI 犯错的责任主体则很难界定,如果对AI的内容进行预先限制,必然会诞生只会说教和车轱辘话的人工智障。
从iPhone 14系列开始,苹果在美版开始推广完全没有实体卡槽的纯eSIM版本,到17系列,开始在更多的地区推广纯eSIM版本,Air系列更是全球统一的纯eSIM方案。
eSIM本身的设计理念是便捷办理、远程激活,在工业设计方面能节省寸土寸金的机身空间给其他元器件,而国行版本最初宣布与中国联通独家合作后不久就被紧急被叫停,直到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特色eSIM的最终模式:线下办理、写卡次数限制、锁死双卡、国行境内禁写外卡、外版无法写入国内卡等等,基于这些合规要求,特色eSIM已经是完全丧失了其最初的设计意义,本末倒置,堪称二十一世纪现代版马拉火车。
这相当于彻底锁死了外版纯eSIM手机在内地的活路,而这也是我买17 Pro Max的原因:eSIM能让寸土寸金的机身减少一个机械结构,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支持实体卡的手机会越来越少。
其实能预见的结果无非两种:越来越多的人用外卡eSIM,或者不知道哪一天国内的eSIM能够写外版机,但我对这一天不抱希望,因为这一切都是科技向审查低头的必然结果,目前国行的iPhone已经因合规需要阉割了AI、Facetime通话、卫星通讯和eSIM数量等等功能,甚至二十年前还一度让国行手机阉割了WiFi功能。
而所有的一切都只因“反诈”这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实名制不仅没有有效控制网络暴力和电诈,反而因信息泄露催生了“定制化精准诈骗”事件的发生,还有近几年愈发猖獗的“开盒”事件。
比起追求效率和国际化标准,增加使用门槛、限制技术自由的审查优先模式已经完全与科技发展本身的意义背道而驰了。
国产机的温水煮青蛙
如果说Apple Intelligence的缺失和eSIM模式的异化是在硬件层面的阉割,那国产安卓机则是在系统底层和应用生态上一步一步蚕食用户的选择空间,如同温水煮青蛙。
早些年大环境就对游戏实施了版号这种限制,在没有成熟分级制度的情况下还能理解,毕竟游戏可能天然带有暴力和非全年龄接受的成分,但到了今天,从游戏版号的限制已经延伸到App上架都需要ICP备案的程度,这对独立的个人开发者来说是极其不友好的,甚至到了除了无法上架以外,还推三阻四的限制了用户自行安装第三方App的程度。
最近我帮一个朋友在华为的平板上安装一些代理工具应用和社交软件,这玩意竟以“诈骗”或“病毒”为由直接禁止安装我下载的APK安装包,断网无法安装,联网拒绝安装,设备自身就成为了审查者的角色。
还有小米手机,直接在固件层面上屏蔽了用户访问境外网站的行为,并对用户解锁BL施加了如高考一样的考试和审核,甚至衍生出了“跑路解锁”的暴力方案,为了限制用户刷写第三方固件和修改系统文件出现这种民间下下策,实属可笑。
最近这六年来我只买过两部Android手机,而且都是外版固件或外版机型,我完全不知道国产手机已经演变成了这样,非常震惊,感觉一瞬间失去了对自己设备的自由掌控权。
无论是系统底层的屏蔽还是对BL解锁的限制,都是为了收窄用户选择的空间,当智能手机不能自由安装应用、不能自由访问网络的时候,智能手机这个曾经象征“新世界大门”的工具也就变成了一个功能被锁定、高度受控的终端,逼迫用户想出“跑路解锁”这种可笑又滑稽的下下策来重新得到本应属于用户的掌控权。
效率至上
现在回头再来看者六年来国内科技环境被“合规”限制产生的种种乱象(或某些人眼里的秩序),从 AI 缺席、eSIM 异化,到系统底层的重重设限,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审查优先的模式已经和高效率和国际化标准产生了近乎“生殖隔离”的差异。
对于原生体验、功能完整和高效率的长期追求,我得出的结论是,我需要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和配置放在一个更广阔,更有流动性的平台之上,我追求的是更灵活、更便捷、更国际化的一种生活方式。
另外,时隔九年半,我会在下周末再次重游香港。
向未来致敬,干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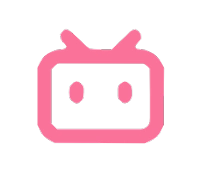






(っ゚Д゚)っ!!システムエラーが発生しました。
現在ご利用の国または地域ではサービス対象外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ネットワーク環境変更後、再度アクセスをお試しください。
※サービス提供地域は利用規約でご確認いただけます。